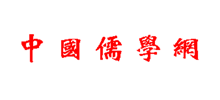孟子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开创者,也是性善论的确立者,但无论是其对人之道德善性之存在根源的追溯,还是“尽心则知性知天”的追求指向,实际上都是一个并未得到确保的开放性体系。从其“此天之所与我者”来看,这一道德善性之天道依据不仅是通过人之“秉彝”来“遥接”与“遥承”的,而且还需要人“从其大体”之具体抉择与道德实践来承当;而从其“尽心则知性知天”的实践追求来看,则这种通过“尽心”方式所实现的“知”其实也只是具体、部分与观照性的知,永远无法达到性、天合一的地步。如果从殷周政权更替所形成的忧患意识、人文关怀及其历史积淀的角度看,则所谓“天之所与”又永远需要具体的历史际遇和时代势运来落实。这样一来,无论是“人性本善”的天道依据还是作为人生终极追求之“知性知天”的指向,实际上也就既需要人之实践抉择来具体承当,同时也必须一定的信仰蕴涵来作为其天人合德之最后弥合。